我读《我城华语》
- 林言
- 22小时前
- 讀畢需時 7 分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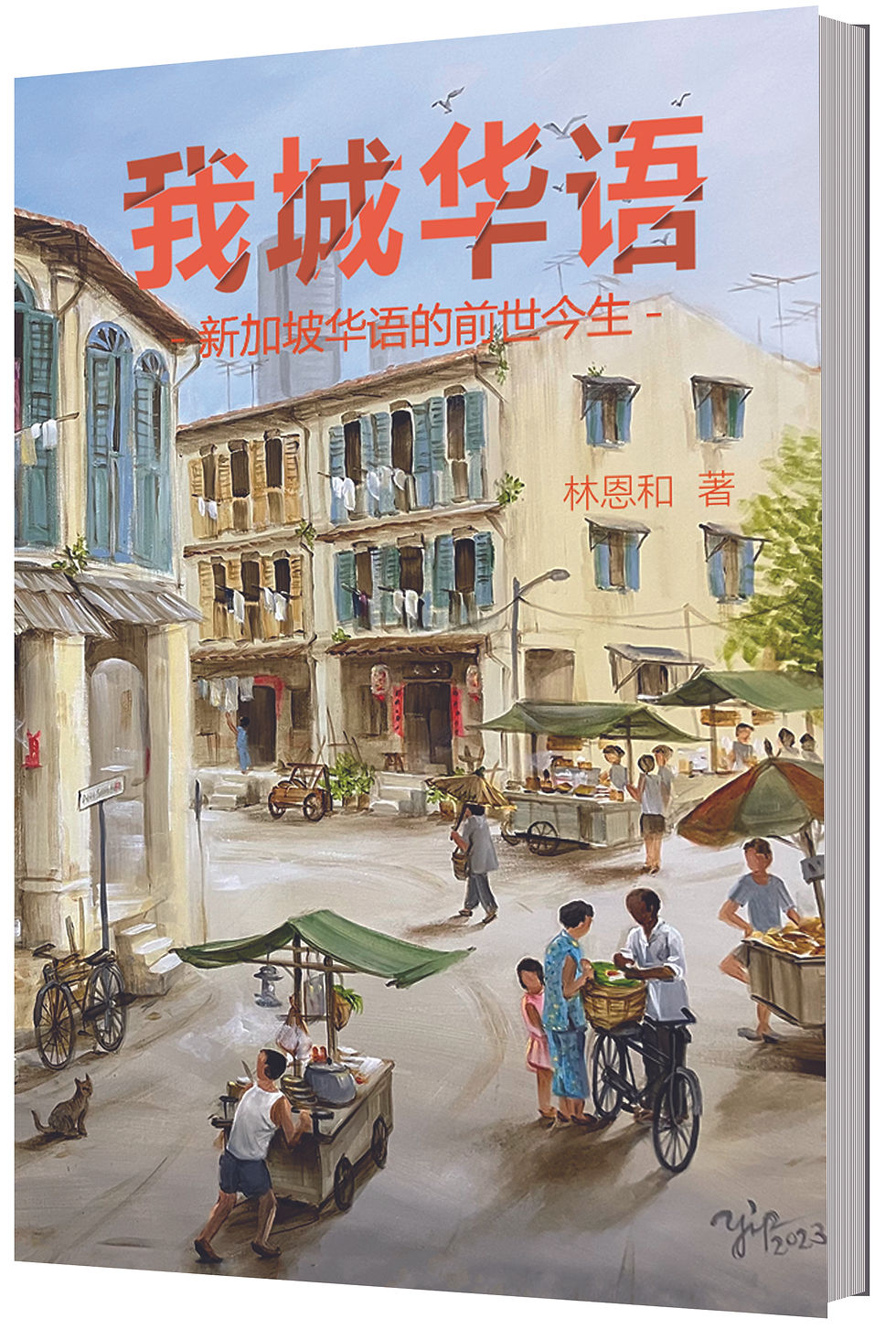
林恩和著《我城华语》分两辑,上辑内容相对轻松,说的是几个词语在新加坡的演变经过;下辑内容相对严肃,讨论的新加坡华语课题,关系到语文生态里的多种社会关系以及华人身份的认同。
“礼拜”与“星期”的倾轧
作者讲解“星期”与“礼拜”的意识形态之争,我特别受益。
原来礼拜一词,最早见自班固所著《汉武故事》:“不祭祀,但烧香礼拜”,说的就是“致礼于所信仰的神佛”,并不包含今日沿用的西方历法的含意。作者指出,要等到十六世纪西方殖民势力东来后,旅居南洋的华人才开始接受七天为一个礼拜的时间观念。在这之前,华人的时间框架只有年、月、旬、日和时。

他引述1620年代出版《西班牙-华语词典》编者的按语:“由于他们没有各个周日的对应名称,因此只好以数字来表达”。哈哈,还好我们的祖先能以自己的造词方式来表达新观念,这样我们就不必像读英文时那样需要多背七个生词。
饱览群书的作者,也引了印度尼西亚华人两部珍贵史书《开吧历代史记》及《公案簿》的记录,证明“礼拜”很早以前已是南洋华侨通用的词语。
中国使用礼拜及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词,相信要比南洋迟了两百多年。作者指出,礼拜的时间观念,在中国社会开始被接受,可能要以1872年上海《申报》的出版为准:(该报)“在创刊号中已使用礼拜这个新词”。不过,礼拜这类外来词,却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严格审视,他们质疑其宗教意涵。作者分析:“中国士绅能接受‘七天一周’的观念,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;但是出于保护固有文化不受西方宗教侵蚀的立场,有必要以民族化的词语来取代‘礼拜’。”
为抵制礼拜的用法,于是报纸书刊上便曾出现好几种代称如:来复、七曜、星期。1908年上海《须弥日报》开始在版头使用星期,接着北京和天津的报纸也跟上。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,正式宣布采用阳历,“在文化自主与民族认同的驱动下,星期的使用成为社会主流”。
新加坡使用礼拜已多年,然而,十九世纪中叶以来,随着国家民族意识在华人社会的萌芽和逐渐高涨,礼拜和星期之争,也蔓延到新加坡。据本书作者查阅,最早使用星期的本地报章应是《振南日报》,时为1914年1月17日。随后跟上的是《南侨日报》和《新国民日报》。至于1923年创刊的《南洋商报》和1929年创刊的《星洲日报》,一开始即以星期记日。
由此比较,新加坡报章要比中国报章较迟使用“星期”。至于“礼拜”,在新加坡华社民间至今还常可听闻。
脚踏车和脚车并行
行文流畅的林恩和,在讲述“脚踏车”、“面包”、“榴”、“胡姬”与“咖啡”等词语的形成和确认过程,也与讨论“星期”这词一样,引经据典,深入浅出,有时还颇耐人寻味。
我很小就羡慕哥哥有脚踏车,却不晓得脚踏车的名称除了脚车外,还有自由足踏车、脚踏快车、足踏快车、自由车、自转车、脚踏单车、单车、单轮迹车和铁马这些称谓。我在六十年代初认识的另一个名称是自行车,那是因为读了一部苏联爱情小说《自行车上的爱情》。自行车在中国是通用词。如今,新加坡人还是脚踏车和脚车并用。作者解释,这两个词能脱颖而出并非偶然,“首先它必须符合当地华族社会的口语习惯,其次它必须由繁化简容易上口”。

南洋的面包物语
面包这种西洋食品,相信最早是由入侵南洋的葡萄牙人传到东方来的。他们在澳门留下一部《葡汉辞典》,便收有面包和面包铺等词语,那是1580年代的手稿。较后在菲律宾留下的则有西班牙殖民者的踪迹,是《西班牙-华语词典》,书里用的是馒头来称呼西方人的面包,不造新词。荷兰人到了印尼,华人的文字记录里最先却是以“劳智”(闽南语roti的译写)称呼。英国人踏足新加坡,面包自然是主要食品。1887年刊行至1932年的《叻报》,面包是常用语。
作者指出,面包早被新加坡作为书面语,民间却常称之为“ 地”,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的反映。
榴梿还是榴莲?
榴这种南洋特产,早于十五世纪初,便见诸三宝公郑和随从马欢的《瀛涯胜览》:“有一等臭果,番名赌尔渊。……若臭牛肉之臭……甚甜美可吃。”赌尔渊便是马来语durian的译音。
福建龙溪人王大海曾侨居爪哇10年,1791年写的《海岛逸志》,称榴为“流连”。广东人谢清高1792年口述的《海录》,则称“流连子”。
1819年新加坡开埠后,南来中国文人墨客何其多,提及这异果的自然不少,如:榴连、流璃、罐果、留连。1920年代,两大华文报章则较常以“榴莲”为名。据作者考究,1947年出版的《复兴国语教科书》,首先把榴写为“榴”。1960至1970年代,作者统计,两大报刊登榴有500例,榴莲200多例,榴连80多例。中国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六版,则以榴为主词条,榴莲为副词条。

胡姬非兰花?
1932年马来亚胡姬学会主办第二届胡姬花展览会,《星洲日报》以兰花称之,《新国民日报》则以“香兰”名之。1935年出版的《新加坡指南》,则以音译“奥吉兰”为胡姬。1939年胡姬花首次出口欧洲市场之后,在华文报章的报道里,胡姬的音译更是五花八门,如:乌吉、奥杰、乌乞、奥植等,也有采用兰为中心词者如:野兰、香兰花、西洋兰花、洋兰花和寄生野兰等。
据称,为胡姬名称一锤定音的,则是南洋美专创校校长林学大。他给自己的作品取名《胡姬》,时为1947年。1953年版的《国语》课本,便以胡姬来指称本地的兰花。不过,作者察觉,在这之前出版的教科书,多数还是采用兰花一词。
作者指出:“胡姬花在新加坡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上,被赋予多重的象征意义和使命……其存在的合情合理是毋庸置疑的。”此外,他也察觉胡姬和兰花在新加坡的语境中,其实各有不同的意涵。
咖啡还是羔丕好喝?
不讲不知道,原来咖啡的阿拉伯语词源qahwa,在咖啡还没成为日常饮料时,是泛指含麻醉或兴奋作用的饮品。后来,咖啡传入欧洲,竟成为一种时髦饮料。欧洲对咖啡的需求大增,荷兰人便在爪哇强制推行咖啡树种植制度。
“爪哇原生态农业惨遭殖民和资本的破坏,看似天灾,其实是彻彻底底的人祸。爪哇农民付出惨重的代价,换来荷兰的财富不断地累积。”所以,本文的题目是《沾上殖民血腥的“咖啡”》。
印尼华人的历史文献《开吧历代史记》,以“高丕”称咖啡,后来也称为高丕茶、戈丕、羔丕。1837年在新加坡出版的《每月统计传》,首次见到咖啡这个词。
咖啡的通行,可见诸1887年《沪上杂记》的一首打油诗:大菜先来一味汤,中间肴馔辨难详。补丁代饭休嫌少,吃过咖啡即散场。
1915年《中华大字典》收入咖啡一词,结束了咖啡诸多别称的情况。可是,新加坡两大报直到1976年,还会偶尔出现“羔丕”等其他称呼。
本书作者于此指出:由于新加坡长期受到殖民统治,官方从不协助推广华语或主导编辑词典规范华语,再加上新加坡华社由各个方言族群组成,因此,像“羔丕”这样的色彩浓厚方言词,便有了长期存在的土壤。

洞察秋毫 仗义执言
《我城华语》下辑收集的五篇文章,讨论可说是意义更加深远的课题。这里仅引述几段文字,很能说明作者林恩和在研究华语的各种问题时,凭的就是作学问的细致推理、洞察秋毫和仗义直言。
他反对以所谓的“华语语系论述”理论来论述新加坡华语:“把汉语排除于华语圈之外,在学理上和心理上,刻意置入反华、反共的基因,造成与汉语对立,建构自立于大华语正统之外的独立语言,成为他们反对所谓‘中华帝国’政治,反对‘帝国语言霸权’的意识形态。”
他强调,新加坡华语的独特性以及与汉语的差异,只反映了新加坡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,而不存在与原乡语言对抗的因素。
他观察到,我国新一代政治领袖已意识到,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,容许一种具有本身个性的地域性华语存在,对建立共同的国家意识和华族国民的身份认同,不无裨益。
在回顾新加坡华语的遭遇时,他认为新加坡呈现的是“双层语言”而非双语的现象,英语在上,其他所谓的官方语言在下,因此,乃不无慷慨地指出:“新加坡华语在过去,它的发展只能依靠华社民间力量和资源来推动,庆幸的是在独立前,新加坡华社以坚忍不拔之志,建立了完整的华文教育系统,华校教科书成为新加坡华语规范化的重要推手,对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定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”
维护新加坡的多元文化
在《新加坡华语告别“母语”》一文里,林恩和举了两个例子,尤其叫人心寒。一是朋友因为读不懂英语告示牌,竟然被人恐吓要报警:“你们去向警察说你们不懂英文好了!”原来在某些新加坡人眼里,不懂英语也有罪。
另一个例子是教育部副提学司李廷辉1971年发表在《南洋商报》的文章,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新加坡的政治现实:“新加坡当前的政治情况是受英文教育的中层阶级华人当权,……在长期方面……他们是要使到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变成受英文教育。”
英文媒体包括好些学者如陈颖芸,便公开主张新加坡“可以也必须把英语当作母语”。
在《新加坡华语还有明天吗?》一文里,林恩和指出,作为体现多元族群社会的特征,我们所熟悉的多元文化、多种语言的环境,已逐渐离我们远去,新加坡正逐渐呈现单元化的语言环境和单元化的文化状态。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因此说:“这么做却刻意减少、简化了我们的文化基因,以及历史所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。”
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,我们必须“重新确认华文华语在国家建设中的价值,将它置于建设多元文化的高度来思考,并把它当作我们国家的珍贵的文化遗产,以保护文化资产之心来保护。”我们都相信:“子规夜半犹啼血,不信东风唤不回”。愿大家共勉之。
作者为独立撰稿人

留言